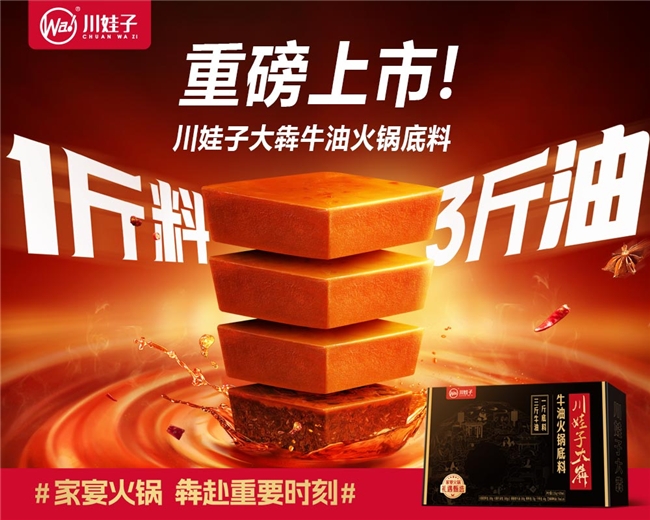中華美食文化何以一路走來、驚艷世界

正在熱播的電視劇《尚食》,站在明清這座“食文化”高峰的起點上,試圖展現(xiàn)中華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人們對電視劇的評價并不高,但其引出的話題卻頗有價值,即中華美食文化何以一路走來,最終綻放出絢爛的華章?
——編者
時至今日,中國食客們早已習(xí)慣了“中華美食甲天下”的尊榮,街邊商廈林林總總的小吃店,墻上往往喜歡掛一段上逾千年的傳說——雖然食客大多也不會把這些動輒與乾隆、諸葛亮、秦始皇甚至是黃帝、女媧的故事當(dāng)真,但換個視角將華夏五千年歷史視為五千年美食史,似乎也不算太夸張。
然而,歷史真相往往令人感到意外。中國歷史雖然源遠流長,但中華美食文化其實異常晚熟:“南食”“北食”直到唐宋時期才逐漸分野,土豆、玉米、番茄、辣椒等食材直到明代才傳入,“四大菜系”直到清初才成型,而當(dāng)“八大菜系”隆重登場時,中國封建時代已經(jīng)走向了尾聲。不少如大盤雞、螺螄粉這種人們習(xí)以為常的小吃、菜肴菜式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才誕生,而“菜系”作為一個專有詞條,直到1992年才被收錄到《中國烹飪辭典》中。
沒錯,中華美食的確博大精深,但它的成長之路卻也曲折縈紆,歷經(jīng)磨難。
了解到中華美食榮光背后的漫漫長路,在物質(zhì)生活極大豐富的歲月里,食客們或許會對“一粥一飯,當(dāng)思來之不易”這句古訓(xùn)有更深的感悟。中華美食是美好的,華麗的,精致的,同時也是堅韌的,頑強的,隱忍的。中華美食文化是古老悠遠的,同時也是大器晚成的。三代以降,五千年時光仿佛是一場漫長的蟄伏,為的只是在某一個時間,爆發(fā)出最絢爛的華章。
更值得回味的是,這一個爆發(fā)的時段,正是中國人面對大變局積極吸收先進思想和制度,重塑華夏榮光的時代。其實,飲食之道、為人之道、謀國之道,在某種層面上也是相通的:食客們觥籌交錯之中、在推杯換盞之時其實不難發(fā)現(xiàn),中國美食自古以來最不缺的,就是兼容并蓄的氣度和能力。倘若孔子泉下有知,見到這一幕大約也不會再堅持“君子謀道不謀食”了吧——謀食之道里,自有一個民族最堅韌的初心。
“民以食為天”逼出的想像力
司馬遷所引的“民以食為天”,指的不是百姓對食物的盲目熱情,而是傳統(tǒng)農(nóng)耕社會生存壓力的寫照。作為農(nóng)業(yè)古國,中國較之其他文明更早出現(xiàn)了人口生態(tài)壓力,這一壓力在締造了靈渠、都江堰、大運河等奇跡的同時,也極大激發(fā)了中國人對食材的想象力。
中國人的美食追求并非天然通向“味道至上”。先秦以降,中國飲食與養(yǎng)生、醫(yī)療結(jié)合得更為緊密,兩漢時期讖緯之學(xué)與仙道之風(fēng)盛行,飲食養(yǎng)生的風(fēng)氣遠較宴席間的觥籌交錯更吸引士大夫階層。歷史悠久的辟谷習(xí)俗,從某種角度來看甚至是反美食主義。
后人言及“盛世”,大多會將目光指向漢唐兩代。這兩個朝代,國家統(tǒng)一、文化昌明、武功強盛、國威遠播,直到幾千年后,“漢字”和“唐人街”依然是中華文化的代名詞。然而即便是這兩個朝代,中國人的糧食危機也不絕于史。《漢書》中動輒出現(xiàn)“大饑,人相食”“饑,或人相食”的記載,而唐代皇帝曾十余次因缺糧暫時遷都洛陽,留下了“逐糧天子”“就食東都”這個歷史名詞。帝尤如此,民何以堪。
窮則思變,在巨大的糧食危機面前,也不由得古時的中國人對食物不具備足夠的想像力。三國時期,中原動蕩不安,天下四分五裂,曹操一邊感嘆著“白骨露於野,千里無雞鳴”,一邊編著了中國第一部獨立飲食著作《四時食制》。南北朝時期,戰(zhàn)爭連年不斷,自然災(zāi)害頻發(fā),集北方民間減災(zāi)思想和經(jīng)驗之大成的著作《齊民要術(shù)》應(yīng)運而生。金朝入主中原,宋室及北方士大夫階層大舉南遷后,以水稻栽培為主要內(nèi)容的《陳敷農(nóng)書》問世。元朝借助強大的騎兵締造了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帝國,但也讓無數(shù)肥沃富饒的田地變得滿目瘡痍,司農(nóng)司受命編著官書《農(nóng)桑輯要》,之后王禎《農(nóng)書》、魯明善《農(nóng)桑撮要》幾乎同時出現(xiàn),這一系列農(nóng)學(xué)方面的成熟絕非偶然的巧合。
掩卷,又不得不聯(lián)想到中華美食的烹飪技法和食材范圍,相較于其他國家的菜系簡直到豐富到令人咋舌的程度,這是不是因為生存狀況倒逼而形成的想像力呢?
“五谷雜糧”隱藏的包容性
如果說盡可能提高食材的利用率是“節(jié)流”,那積極引入外來物種為己所用就是“開源”;如果說“節(jié)流”表現(xiàn)了中華美食背后的地大物博,那“開源”則揭示了中華美食文化的兼容并蓄。
俗語有云:“人食五谷雜糧,孰能無疾。”“五谷”,可以說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代表。“五谷”有兩種說法,一是鄭玄認為的“麻、黍、稷、麥、豆”,二是趙歧認為的:“稻、黍、稷、麥、菽”。無論哪一種說法,麥——這里主要指小麥,都是中國人自古以來最重要、最普遍的主食之一。
然而,小麥并非中國土生土長的農(nóng)作物。換句話說,支撐起中國幾千年文明、給中華美食帶來無限榮光的小麥,其實是個貨真價實的舶來品。小麥起源于新月沃地,在甘肅民樂東灰山遺址、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溝等西北地區(qū)分別發(fā)現(xiàn)了公元前兩三千年的小麥遺存,這讓后世的考古學(xué)家大致能勾勒出小麥傳入中國的路線。小麥古稱“麳”,在甲骨文中,“來”為小麥植株形象,“來”的“行來”之義正淵源于小麥的舶來品身份。當(dāng)然,小麥的本土化也經(jīng)歷了數(shù)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,直到北宋時期,中國農(nóng)人才在土壤耕作、種子處理、栽培管理等技術(shù)層面積累到了足夠的經(jīng)驗知識,讓小麥在北方種植制度中取得了核心地位。
中國的主食,有“北面南米”之稱,這背后是農(nóng)作物上的“北麥南稻”。中國是水稻的原產(chǎn)地之一,這毋庸置疑,但在古代中國“華夷秩序”的視野下,水稻來源于百越族先民的馴化,其實也并非純粹的中原物產(chǎn)。大禹曾在黃河流域嘗試推廣稻作,對于以河南、河北、山西、山東為中心的夏王朝來說,大禹的作法無疑是一次物種引進的嘗試,只是因為這一引進史過于久遠,而長江文明最終與黃河文明一道成為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,因而被淡忘了。
但即便如此,關(guān)于水稻的引進史也并沒有停止,《宋史·食貨志》載:“大中祥符四年(1011年)……帝以江淮、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,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,分給三路為種,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,蓋旱稻也……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,粒差小,不擇地而生。”這里提到的占城稻,即源于古代越南南部的小國占城。占城稻適應(yīng)性強、生長期短,因而在大中祥符被引入長江流域,以應(yīng)對災(zāi)荒之困。
20世紀40年代,正值中國抗日戰(zhàn)爭最為艱苦的時期,東北地區(qū)流傳了一首悲憤激昂的《松花江上》,起首一句便是:“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,那里有森林煤礦,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。”
“高粱”二字,很東北,也很中國,但不要意外——高粱的原產(chǎn)地不是中國,甚至不是東亞,而是遙遠的非洲。高粱傳入中國的時間與路線更難考證,因其早期有“蜀林”“巴禾”之稱,可能是由西南地區(qū)漸次傳入中原,直到宋元兩代成為北方人的重要主食。
除了主食,中國人對蔬菜瓜果更是海納百川。中國人的菜譜上,有三類食材從名稱就能看出其“海外血統(tǒng)”:第一類名稱中帶“胡”,基本于漢晉時期由西北陸路引入,主要有胡豆(蠶豆)、胡瓜(黃瓜)、胡蒜(大蒜)等。胡蘿卜也源于西亞,但傳入中國的時間稍晚。第二類名稱中帶“番”,主要于南宋、元明及清初由番舶引入,如番茄、番薯(紅薯)、番椒(辣椒)等。第三類名稱中帶“洋”,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,洋蔥、洋芋(馬鈴薯)、洋白菜(甘藍)等。如今,這些外來物種早已融入中華美食,甚至成為某些食物的靈魂所在——沒有了蒜泥,火鍋會黯然失色;沒有了辣椒,整個川菜都會“啞火”;沒有了番茄,多少人學(xué)會的第一個炒菜(番茄炒蛋)恐怕也要變個名稱了……
《隨園食單》背后的鉆研心
中國食客說起中華美食之道,往往喜歡引用孔子的“食不厭精,膾不厭細”八個字。其實,孔子所言的“食不厭精,膾不厭細”,更側(cè)重于祭祀時飲食的態(tài)度而非對味道的追求。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,烹飪、碓舂、切肉工藝均相對原始,將“食”做“精”、“膾”做“細”,體現(xiàn)了廚人與食者嚴肅真誠的態(tài)度。與此相對,孔子針對口腹之欲多有“君子食無求飽”的論斷,追求食物的奢華精細,本身便與孔子的理念背道而馳。
孔子的飲食觀背后,是其心懷的禮制。其實中國人與食物最早的聯(lián)結(jié)不是味道,而是禮儀。《禮記》所言“夫禮之初,始諸飲食”,大意即是“禮儀制度和風(fēng)俗習(xí)慣始于飲食禮”;而據(jù)《周禮》所載,周王室四千多名治官中一半以上的職責(zé)與飲食相關(guān),細品之余不難發(fā)現(xiàn)上古食物與生俱來的森嚴與拘謹。春秋時期最著名的廚師——同時也是后世廚師的“祖師”易牙,其精致的廚藝與其說是職人的素養(yǎng),更不如說是史書為勾畫其殘忍而加的腳注,從中也不難口味到美食與美德之間隱隱的矛盾。
古代中國對食物的“淡漠”不僅出于食材的緩慢積累、交融,更在于儒家文化對口腹之欲的“打壓”。一方面,孔子“君子謀道不謀食”的教誨讓士大夫階層往往遠離庖廚而以修齊治平為己任;另一方面,自漢武帝劉徹“罷黜百家獨尊儒術(shù)”后,士大夫階層仕途通暢,“學(xué)而優(yōu)則仕”也有著豐富的現(xiàn)實回報。至晚在唐代之前,文人對于飲食之事是少有重視的。
隋唐時期飲食文化尤其是宴席之風(fēng)雖有較大發(fā)展,但在盛世文治武功的影響下,士大夫階層的追求依然在“提筆安天下、馬上定乾坤”之中,“烹羊宰牛”式的盛筵并沒有孕育出與之相當(dāng)?shù)娘嬍澄幕L拼O一時的燒尾宴,也只是公卿士大夫的盛宴,遠非平民百姓所能享受。
轉(zhuǎn)折來自于兩宋:從個體角度來看,兩宋文化昌盛導(dǎo)致讀書人與日俱增以至于仕途門檻抬高,同時武功疲弱又令多少人雄志難酬。從朝廷角度來看,宋室有鑒于唐朝藩鎮(zhèn)割據(jù)之痛,自宋太祖趙匡胤“杯酒釋兵權(quán)”始便鼓勵朝臣“擇便好田宅市之,為子孫立永遠之業(yè),多致歌兒舞女,日飲酒相歡,以終其天年”。用舍行藏之下,也不由得士大夫們不將視線轉(zhuǎn)向飲食了。北宋蘇軾以嗜美食聞名,而其半生謫居的仕途,多多少少也體現(xiàn)了當(dāng)時的飲食與儒家傳統(tǒng)追求此消彼長的關(guān)系。
元朝統(tǒng)一后,漢族士人愈加邊緣化。明清易代,朝廷中樞又多為滿族壟斷,“學(xué)而優(yōu)則仕”的路途不再暢通無阻,文人的興趣自然而然愈加轉(zhuǎn)向犬馬聲色。如以“小品圣手”名世的張岱,便在《陶庵夢憶》中洋洋自得地夸口“越中清饞,無過余者”,從北京的蘋婆果到臺州的江瑤柱,從山西的天花菜到臨海的枕頭瓜,大明兩京一十三省的美食竟被他嘗了個遍。又如戲曲大家李漁,一邊醉心于梨園之樂,一邊也不忘鮮衣美食這一類“家居有事”,并在理論巨著《閑情偶寄部》中加入“飲饌”一部,系統(tǒng)闡述其“存原味、求真趣”的飲食美學(xué)思想與“宗自然、尊鮮味”飲食文化觀念。
特殊的時代背景使得“飲食之人”不再被輕賤,于是一大批美食家在清代前半葉應(yīng)運而生,在這一背景下,“食圣”袁枚登場了。
袁枚在《與薛壽魚書》公然提出“夫所謂不朽者,非必周、孔而后不朽也。羿之射,秋之奕,俞跗之醫(yī),皆可以不朽也”,而他自己則將飲食之道視為堪與周公孔子之為相媲美的事業(yè),因此可以毫無顧忌地“每食于某氏而飽,必使家廚往彼灶觚,執(zhí)弟子之禮”。
袁枚作詩以“性靈說”為主張,認為詩直抒心靈,表達真意,這一主張也融合到了飲食中:他認為在烹飪之前要了解食材、尊重物性,注意食材間的搭配和時間把握;他反對鋪張浪費,提出“肴佳原不在錢多”,食材之美更在于物盡其用;他將人文主義引入飲食,宣揚“物為人用,使之死可也,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”;他強調(diào)烹飪理論的重要性,以為中國烹法完全依廚人經(jīng)驗不利于傳承,為了給后世食客廚人樹立典范,又煞費苦心撰寫出了《隨園食單》——這部南北美食集大成之作,再一次為中華美食的發(fā)展開啟了新的紀元。
《隨園食單》之前,中國歷代亦不乏飲食著作,但關(guān)于制法的記述往往過于簡略,如《食經(jīng)》《燒尾宴食單》之類甚至流于“報菜名”。宋元以降,飲食著作的烹飪方法逐漸明晰,但亦停留在“形而下”的層次。而《隨園食單》則完成了飲食文化從經(jīng)驗向理論的最終蛻變。如“須知單”“戒單”中梳理了物性、作料、洗刷、調(diào)劑、搭配、火候、器具、上菜等方方面面,“上菜須知”中的“鹽者宜先,淡者宜后;濃者宜先,薄者宜后”等,都是對中國千年烹飪經(jīng)驗一次開創(chuàng)性的總結(jié)與編排。
在袁枚和他的《隨園食單》之后,中國飲食文化從“形而上”的思想層面邁上了一個新臺階,在之后的百余年里,幫口菜漸漸發(fā)達,“四大菜系”“八大菜系”逐漸成形,直到清朝國門被堅船利炮強行打開時,孫中山在《建國方略》中依然能夠自信地寫下:“我中國近代文明進化,事事皆落人之后,惟飲食一道之進步,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。”
來源: 文匯報
冷鏈服務(wù)業(yè)務(wù)聯(lián)系電話:19937817614

華鼎冷鏈是一家專注于為餐飲連鎖品牌、工廠商貿(mào)客戶提供專業(yè)高效的冷鏈物流服務(wù)企業(yè),已經(jīng)打造成集冷鏈倉儲、冷鏈零擔(dān)、冷鏈到店、信息化服務(wù)、金融為一體的全國化食品凍品餐飲火鍋食材供應(yīng)鏈冷鏈物流服務(wù)平臺。
標簽:
下一篇:管窺飲食文化的特色

 冷鏈新聞
冷鏈新聞 企業(yè)新聞
企業(yè)新聞 展會新聞
展會新聞 物流新聞
物流新聞 冷鏈加盟
冷鏈加盟 冷鏈技術(shù)
冷鏈技術(shù) 冷鏈服務(wù)
冷鏈服務(wù) 冷鏈問答
冷鏈問答 網(wǎng)站首頁
網(wǎng)站首頁 冷鏈新聞
冷鏈新聞